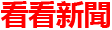△ 2 月 18 日,廣東東莞望牛墩鎮街頭巷尾都有廟,春節時香火旺盛。齊海兵在東莞南城做室內設計,周末過節都會來望牛墩父母傢。大年初三早上,他跟妻子逛七夕公園,在文峰塔前為即將降生的孩子許瞭一個美好的願望。 圖 / 唐兵兵
△ 2 月 18 日,廣東東莞望牛墩鎮街頭巷尾都有廟,春節時香火旺盛。齊海兵在東莞南城做室內設計,周末過節都會來望牛墩父母傢。大年初三早上,他跟妻子逛七夕公園,在文峰塔前為即將降生的孩子許瞭一個美好的願望。 圖 / 唐兵兵
大年初二下午,東莞望牛墩鎮溫度 22 ℃,年味很淡,有些寂寥。
這個在 1984 年就被授予 " 億元鄉鎮 " 的嶺南小城,在改革開放以後,吸引瞭無數的湖南打工者。在完成瞭工業的粗放、原始的積累之後,大量工廠倒閉,建設萎縮,小鎮面臨著轉型。
而第一代南下憑借氣力做活的湖南打工者,已經開始老去,顯然沒辦法跟上這趟轉型的列車瞭。不過,對於他們來說,離開,同樣艱難,像再一次離開故鄉。
" 往前兩年,過年都是很熱鬧的,這條街上擁擠得很呢。" 那時,齊庭秀正帶著我走過紅橋,紅橋兩岸是小鎮最繁華的區域,此時不過寥寥幾個行人。" 現在小車多瞭,回去過年方便。" 這是他的解釋。
留在廣東過年的湖南人依舊不少,短短幾百米的路程,齊庭秀就遇到瞭三四撥同鄉,不免相互寒暄,敬煙,互道 " 新年好 "。
齊庭秀也說不清傢鄉究竟有多少人在望牛墩,街旁坐在石凳上聊天的是老鄉,支起桌子打牌的也是老鄉,寒暄竟然有些忙碌,齊庭秀的一包煙很快就散完瞭。齊庭秀是永州新田知市坪鄉人,和我同鄉。
他的村莊跟我的村莊,不過兩公裡路程,在廣東小鎮裡竟然一路鄉音,讓我有回到傢的恍惚,很快對這個小鎮親切起來。
相比在傢鄉過年時節的忙碌,廣東過年的老鄉們顯然閑適得多。吃過飯人們都不約而同來到河邊聚集,或閑聊或打牌,打牌是湖南流行的三打哈,外人無法參與,也不容許外人參與,這是約定俗成的規矩,怕外人出老千,更深層的原因,是外人贏瞭錢,沒有下次扳本的機會。
婦女們則更喜歡端著自傢的剩菜,呼朋引伴聚集,組一個茶會,茶會依舊是傳播新聞、傢長裡短的最佳場所。他們不像是一群異鄉人,倒像是這個小鎮的主人。
" 冬天湖南太冷瞭,冬天都起不來床,又得去拜年,不如這裡舒服安逸。"
坐在河邊聊天的一位婦女穿著單衣,在太陽裡伸瞭個懶腰,開啟瞭一場為什麼不回老傢過年的探討。
張小軍並不認同那位婦女的說法,他覺得異鄉總也比不上傢鄉的過年氣氛。
隻是,如今他的親戚都大部分來到東莞,母親也在兩年前接瞭過來," 過年就是為瞭團圓,親人都在這裡,也就沒有回傢過年的必要瞭 "。他傢大年初一的聚餐中,他細算瞭一下," 有 38 個親戚朋友,還有 38 個也在東莞或周邊的鎮上,沒來。
不過,今年,一定要回傢過年瞭。" 張小軍說得堅定,像是對某個人,更像是對傢鄉的承諾。而對於去年活不多的張天生來說,回傢過年依舊像一道難以逾越的 " 關 "," 回傢過年,落腳的地方都沒有,再說起碼要花費一兩萬吧,一年就白做瞭 "。張天生更願意在平時回傢,以避開花銷巨大的 " 年關 ",在廣東過年,更像是一種無奈的逃避。
這些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南下廣東闖蕩的第一代打工者們,青絲成白發。
他們的孩子已經長大,成瞭新的闖蕩者。
不少人傢裡的老人已經離開,他們少瞭牽掛,似乎缺少回鄉過年的理由。
不過,他們大部分終究會離開這裡,回到故鄉。" 過幾年,做不動瞭,就回老傢。"
這幾乎是所有第一代打工者的計劃和退路,隻是,對於歸鄉,誰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。他們習慣瞭城市,已經難以應對撂下幾十年的農活,也難以習慣鄉村的生活瞭。
對於這個他們生活瞭近三十年小鎮的情感,他們從來不輕易表露。隻有他們出生在這裡、已經忘記鄉音、說著一口普通話的孫子孫女,才會天真地說出爺爺奶奶內心隱秘、羞於表達的愛與不舍:" 我有兩個傢,一個在湖南,一個在廣東。"
瀟湘晨報記者唐兵兵